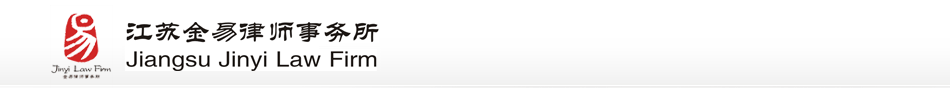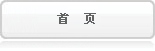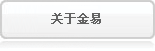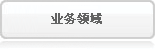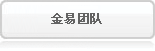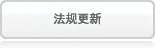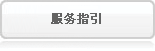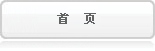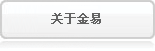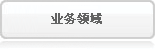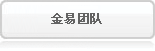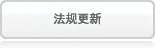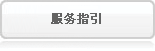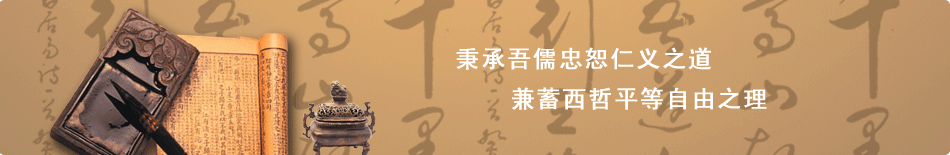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哈罗德•伯尔曼
关于信任和信仰的问题,本来应是一个研究哲学的人考虑的课题,但是作为法律从业人员,当面对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的时候,当看到人们渐行渐远地将法律庸俗化、工具化的时候,当看到法律武器在权力面前不堪一击的时候,不得不从精神价值角度、从终极目的出发来思考关于法律信仰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对法律的信仰危机和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危机
其实这也是现实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这几年来国内发生的一些事件就是和对法律的信仰和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密切相关,只有正视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才让我们能理性地选择解决危机的方法。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信任问题由来已久,信任度低的现象已经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如消费品领域中,假烟、假酒、毒大米、黑心棉等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三鹿奶粉、欧典地板等知名品牌的曝光更是损害了消费者的信心。经济领域中,企业信用缺失问题十分严重,合同履约率不断下降,经济合同产生的法律纠纷连年上升。各种媒体上充斥着虚假宣传,从上市公司如银广厦、杭萧钢构、大唐电信等虚假宣传到各类电视直销的肆意夸大,后果是对企业、行业的不信任,从而影响了企业乃至行业的生存。晚上八点后广播在肆无忌惮地播放庸俗的、虚假的医药和保健品节目,在文化科学领域中,知名演员假唱、恶意炒作屡见不鲜,学者剽窃抄袭、伪造学术成果的事情经常见诸报端。所谓的专家会经常发表一些匪夷所思的言论,为群众所不齿。在经济、文化领域的信任问题逐渐严重之后,信任问题又蔓延到了政治领域。由于政府的部分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假公济私、奢侈浪费,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不作为甚至乱作为、效率低下,导致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因此部分民众对于政府的举动总是以怀疑的目光进行审视,群体性事件多次发生。在多个部门、行业产生不信任感之后,还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如一些事件经过传播、渲染之后,被直接认定为贫富之间的矛盾,也就形成了贫富之间的不信任,如果这种不信任得不到遏制,就会逐步形成对立的两个阶层,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不信任的公众情绪正在向司法领域漫延。法律的意义是捍卫社会公平正义,是保障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近几年来,全国发生的如南京彭宇案、广州许霆案、湖北邓玉娇案等轰动性案件,引起了诸多的质疑和种种的猜测,法院和法官在这些案件中,受到了多方的压力,在压力之下一些判决与事实和法律可能有所背离。笔者认为,其中的部分判决,如杭州“七十码”一案,对于交通肇事罪已经算是从重的结果,从纯法律技术角度法院判决没有认定被告为自首的确也值得商榷,但很多网民还在大喊判得过轻,还在寻找背后的“黑幕”,究其原因,还是对于法律的不信任、对于司法部门的不信任。另外,司法领域的一些腐败案件也进一步加剧了人民群众对执法者的公正性、权威性的质疑。今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指出:“当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的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 这种不信任的现象已经不是个案,其危害性已经让司法部门的高层感到忧虑。“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现在,法律和司法部门面临着空前的信任危机,如何才能重拾民众的信任?如何才能让法律达到被信仰的高度?
二、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与西方法律信仰是否存在不相容性
西方法律的产生与宗教存在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博登海默说过,“在古希腊的早期阶段,法律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一的。宗教仪式渗透在立法和司法的形式之中,祭祀在司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国王作为最高法官,其职责和权力也被看作是宙斯亲自赐予的”。在古代希伯莱,法律即《摩西五经》,就是宗教;在基督教中,信徒们都认为将来会到上帝那里去接受最后的审判;直至今日,在某些伊斯兰教国家里,宗教经典仍被奉为法律。西方著名学者哈罗德•伯尔曼认为,人类学的研究证实,在所有的文化里,法律和宗教都共同具有四种要素:法律和宗教都共同具有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可以说,西方的法律传统浸渍了宗教的影响,人们对法律的理解,不只是认为法律是社会性的、工具性的、仅为秩序而秩序的存在,更是具有一种神圣性的、终极性的体验。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只有短暂历史的国家,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是他们的宪法。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尽管文化大革命对儒家文化有着短时间的批判和破坏,但是,其内在强大的文化传统已经融入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里。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即,能够唤起人尊崇、甘愿践行其原则的,是德与礼,而不是法。儒家思想是将法置于德与礼之下的。
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儒家思想的社会秩序逻辑是身份型的情感逻辑,而不是契约型的法理逻辑。当我们评判一件事物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往往不是是否符合法治的要求,而是考虑是否符合“仁义礼智信”的人际要求,例如,当某人因为行贿而被逮捕,在看守所历经数日仍拒绝说出受贿者的名单,也许有人会谴责其对法律的违背和对执法者的挑战,但是,相信从道德层面称其为“义”的评论也绝不会少。就政府与百姓的关系而言,儒家思想关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提倡官员要亲民勤政,爱民如子,但是另一方面,父母热爱和善待子女,子女怎么可以有怀疑、批评甚至反对父母的念头?就正义而言,中国人从来没有接受西方形式正义、程序正义的法治思想,而是从本质具有实质倾向性的道德观来审视一切,唯有符合人们主观性的道德评判的才是符合正义的,这就产生了在交通肇事案中法官按照法律顶格判、群众还是不满意的格局,相信辛普森案如果在中国他绝对没有那么好的下场。
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不是中华五千年传统文明所必然的产物,而是移植了来源于西方国家的一套体系,二者之间基因的冲突导致了在中国法律从来没有达到被信仰的高度;现在的现实是我们不得不为法律被人们所信任而苦苦奋斗。
三、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社会责任
法律没有被信仰,没有其神圣性,导致律师这一行业的地位在中国达不到在西方国家律师所享有的地位。尽管西方国家关于贬低律师的笑话层出不穷,但是,基于法律的权威和法治的制度设计,律师是法治大厦不可动摇的基石,在西方国家,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银行都是足以以自己的名义证明一个公民的身份的机构。而在中国,尽管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现代的立法体系,但是,我们作为执业者深深感到法律的日益世俗化,律师职业的日益工具化,律师常常被视为是“受过特殊训练来规避法律的人。” 这是中国律师发挥在构建和谐社会伟大进程中的作用所不得不思考和应对的一个题目,或者说一个挑战。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律师使命》中说:“和谐社会的首先要内容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这一内容也正是律师制度创设的前提和基础。律师职业的出现,不仅仅是苦于对社会生活对这个职业专业技能的要求,更是国家政治建构中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 虽然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将律师上升为公平和正义的化身,但是律师这一职业本身就代表着法治,律师兴则法治兴,反之亦然,法治兴则律师兴 。中国律师必须认识到肩负的使用,锤炼好自我,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精深的专业水平和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去。
律师这一行业,其社会责任的本质和内涵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首先,律师的社会责任应当区别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对象和内容主要表现在企业对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对员工、对消费者、对政府、对债权人、对社区和对环境的责任 ,而笔者认为律师作为法律人,应当区别于企业,其主要的社会责任应当是高举法治的大旗,维护法治的尊严。
从低一层讲,法治是律师职业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土壤,从高一层讲,法治是一个国家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原则。尽管我们在现实中面临种种执业困境,但是,我们应当坚信法治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方向。我们应该坚守心中的信念,坚守道德的底线,要有独善其身的勇气,也要有济世为民的爱心,以自己的力量捍卫社会的公平正义,重树世人心中对法律的信仰。特别是在世人对法治进行怀疑和质疑的时候,我们必须站出来进行鼓与呼。
就具体方式而言,律师职业是与千千万万个当事人进行接触、沟通和服务的职业,律师执业的一言一行都是给当事人、群众和社会传递着法律职业体的信息。我们必须以自己的行动珍惜这一个行业的声誉,维护这一行业的荣誉。律师至少应当向客户、并通过客户向社会传递以下信息:
一是传递法治的信息。要让客户知道法律是神圣的,律师不是法律条文的玩弄者,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律师不会接受客户不合法的要求;律师不是掮客,不会在合法手段之外来帮助客户胜诉。
二是传递诚信的信息。要让客户相信律师是负责任的、可信赖的,律师会向客户严格承担保密的义务,会在利益冲突时会放弃自己的利益,在宣传自己时不会作夸大和虚假陈述;要让客户知道律师不会帮助客户追求不诚实不道德的目标。
三是传递规范的信息。要让客户相信律师是一群有着严格的职业规范和职业操守,而不是一群自由散漫的个体户;律师是所有职业中最尽职最勤勉的之一,律师事务所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监督制度,客户的利益可以得到有效保障。
四是传递公益的信息。要让客户知道律师不是唯利是图的一族,而是有公益心、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他们会积极参政议政,会热心社会慈善,会参与公益诉讼,会承担法律援助。
五是传递和谐的信息。要让客户知道诉讼不是解决争端的唯一之道,律师也不是挑词架讼的始作俑者;律师会鼓励当事人在诉讼中和解,律师会充分沟通各社会阶层的要求,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宁。
尽管我们不能期望人们一夜间对法律产生信仰,但是,我们相信经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可以让人们通过律师这一特殊的法律职业群体看到法治文明和和谐社会的希望之光。
王建明&罗祖智 江苏金易律师事务所